
我和恩师江平的师生缘
(谨以此文庆贺恩师江平教授九十华诞)
何培华

何培华博士与江平教授

何培华博士于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开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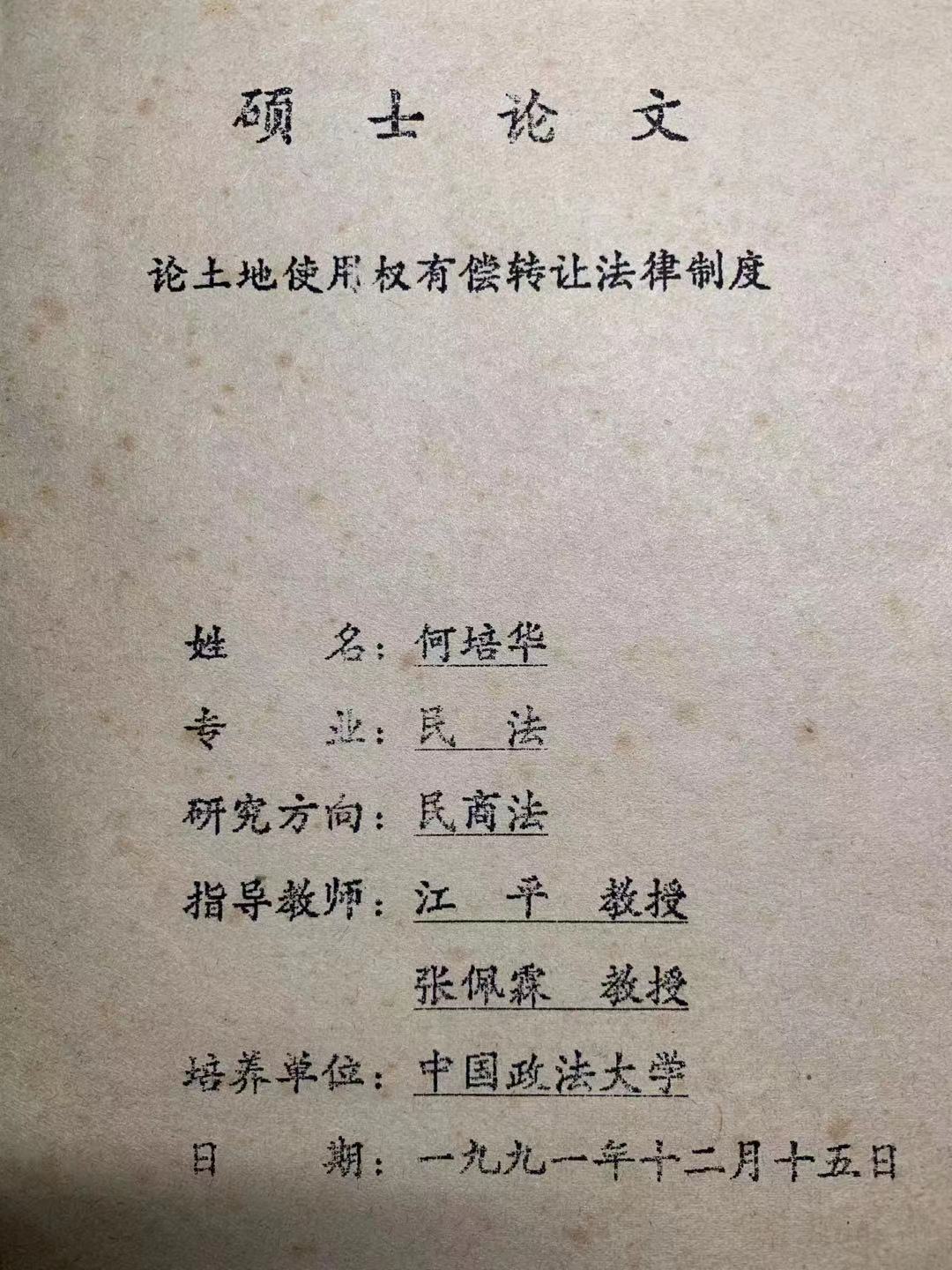
何培华博士硕士论文封面
一九八九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工作,后来因为住房的原因,又调到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对那一年法大校园发生的事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每当谈起当年发生的事情时,江平老师都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学生采取的行动都是合法正当的,我作为一校之长,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学生家长把他们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他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任何问题啊!当时我想,他们出了校门,可能就回不来了。我必须不让他们踏出校门!但是他们人多,我拦不住他们,因此只好跪下来求他们不要出去。他那种舔犊之爱不断溢于言表。江平老师在法大校门口的那一跪,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

法大87级研究生为江平教授及师母祝寿
虽然,我远在广州,但是,我还是不时惦记着江平老师,还是不时关注着他的安危。后来他见到我时笑着对我说,我这个校长的职务是他们给任命的,而不是我伸手向他们要的,他们爱免就免,我并不犯任何错误,干嘛要辞职?我突然发现,一个永不言败的伟岸硬汉形象凸显在我的眼前。一九九〇年二月,在江平老师坚决不同意辞职的情况下,司法部派员到法大,宣布免去了江平老师校长的职务。江平老师虽然不再担任法大校长了,但是,他在我的心中,在法大学子的心中,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永远是我们的校长!
后来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在二000年八月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他还邀请我去纽约大学法学院给研究生做过一次报告。这个案子的材料整整有十二箱,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开庭总共开了五天,从星期一开到星期五,除了事实之外,还涉及到许多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中美之间不同的法律问题。在庭上和美国律师交锋的过程中,我深感到自己法律知识的不足。当年《合同法》刚好颁布,我受托以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名义邀请江老师来广州讲授新的《合同法》。江老师在广州停留期间,我借这个机会把我继续深造的想法告诉了江老师,他和师母听了后,便鼓励我报考法大的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在他们的鼓励下,便报名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一九九九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但非常遗憾的是,我在这次考试中,以一科不及格的成绩名落孙山。可是,我并不因此而气馁,又突发奇想要去美国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进修。为了这个事,我专门跑去北京求助于江老师。江老师听了后,建议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他说我是做律师的,主要侧重实务,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更侧重于法学理论研究,不怎么适合我。哥伦比亚大学有美国律师摇篮之称,比较重视法律实务教学,而且哥仑比亚大学校园位于纽约市中心,在那里学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类精英人物,也可以交更多的朋友,对我将来的律师业务可能更有帮助。他推荐我去找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教授。我非常感谢江老师对我这个晚辈学生的厚爱。回到广州后,我马上给哥仑比亚大学的爱德华教授发了一封邮件,向他提出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申请。江老师给我的推荐信非常管用,爱德华教授收到我的申请后,很快就给我回复,同意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并且还免了我一年的学费。收到爱德华教授的录取通知后,我激动得一夜难眠。如果没有江老师的支持和推荐,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入世界第一流大学法学院学习。他不但是我的严师 更是我的慈父
二〇〇〇年八月,我开始踏上了在哥伦布亚大学法学院为期一年的求学之旅。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我选修了公司法、证劵法、合同法、国际商法等课程。尽管学习任务繁重,我还是保持与江老师和师母的联系。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江平老师七十华诞,纪念活动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举行。我利用学校圣诞节放假的机会,从纽约赶回北京参加是次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有幸聆听了江平老师发表的感人肺腑、激动人心的七十感言。他说:“上天总算是‘公平’的。一九五七年后,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也给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话就是:‘只向真理低头’。”他还说:“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为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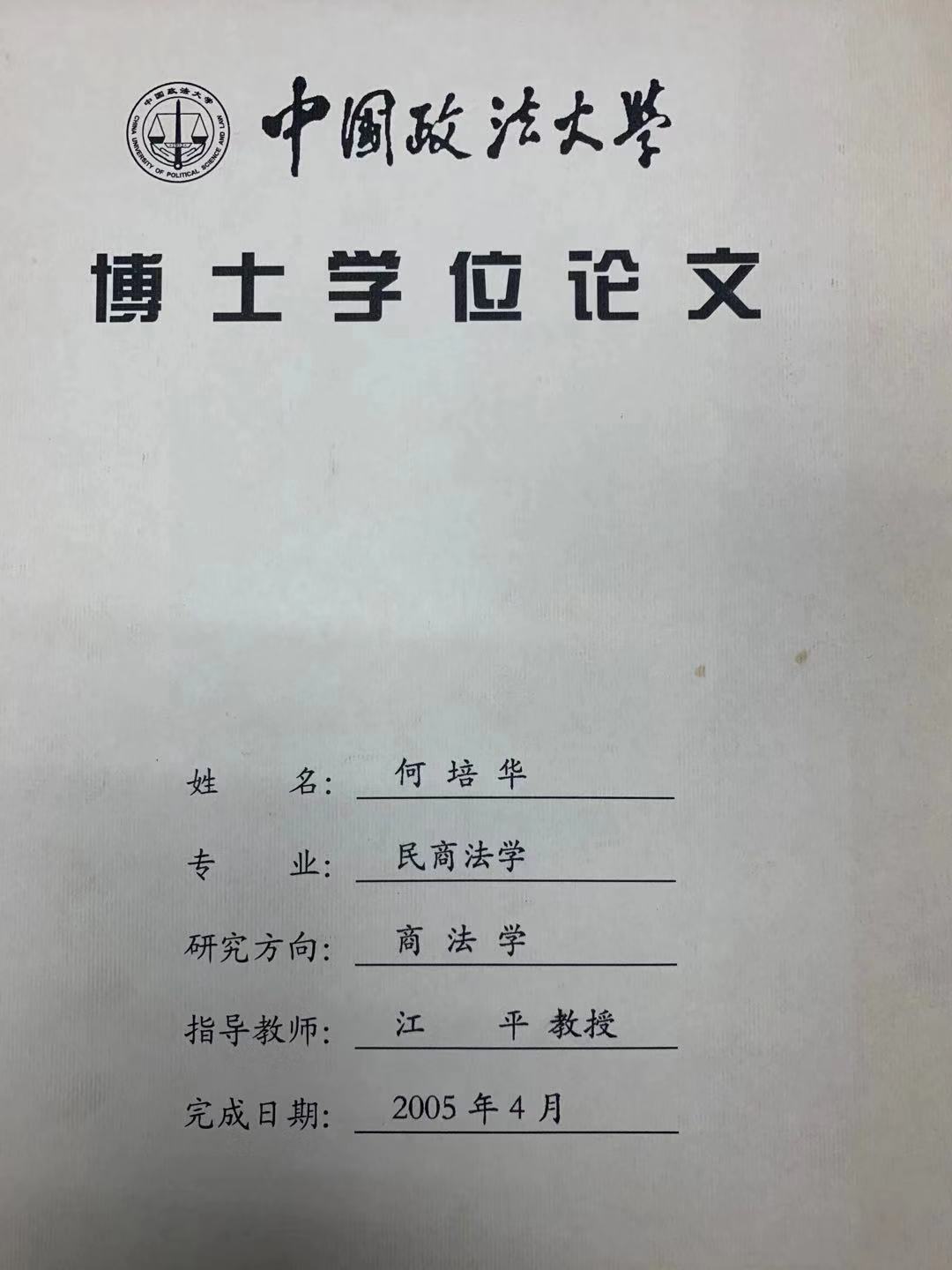
何培华博士博士论文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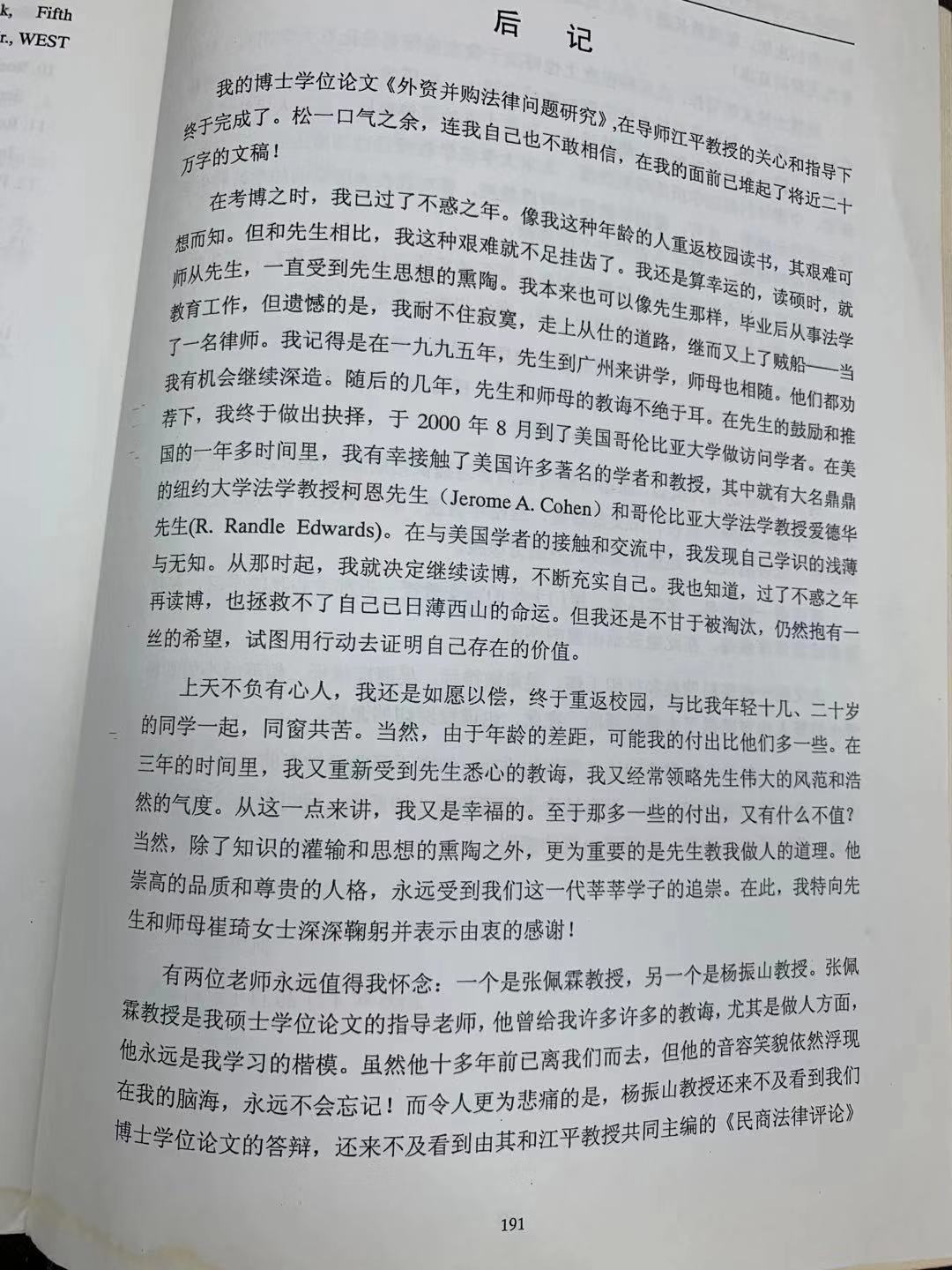
何培华博士博士论文后记

何培华博士与江平教授于中国政法大学

江平教授挥毫寄语何培华博士

何培华博士与江平教授合影

何培华博士与江平教授合影

何培华博士于江平教授八十九岁寿诞
2019年12月19日修改于广州·名雅苑